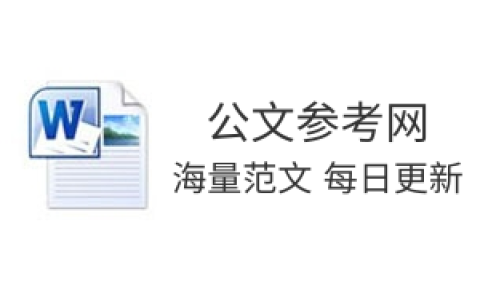在深圳我是一个小会计, 在单位常自称小老百姓.
曾经我以自己即将是一个会计而自豪无比,还没毕业就对外自称是搞财务的。众所周知,在外人眼里(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外行人)做会计的每天与金钱打交道,是老板眼里的大红人,要么是亲戚或者是小蜜,不管怎么着也得是个心腹,我嘛,肯定做不成暧昧的小蜜,那么剩下的红人或心腹随便猜去吧,反正不会小觑我。就这么个未来的会计身份就应该让第一次知道我是财务人员的外行人对我刮目相看(在那个时候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至于碰到同行,老牛拉破车,门当户对,大家彼此心照不宣,连吹牛都可以省了,也犯不着担心谁看不起谁,没参加工作以前,我眼里全是祖国的大好河山,未来形势一片光明。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东莞给一台湾老板做董事长助理,每天七点上班,午夜十二点下班,短短的七个小时要冲凉要洗衣服,偶尔还需要打私人电话,写封信与家人朋友联络感情,中间还得紧张着保安随时会奉老板之命前来差遣我们,辛苦啊!白天上班的时候不允许接任何私人电话,所有的电话老板都有录音,手机还不流行,我没钱也没想到去买。工作也并不是十七个小时都排的满满的,可以到原材料仓库或成品仓库躲着聊天(用口,单位只有一台电脑在每天早上八点至十点两个小时可以上网,用来接收美国客户产品订单)、发呆,也可以在厕所里多呆一会儿偷懒(但如果老板突然想起来有什么事要问我,在男保安不能在正常我会出现的地方找到我时,两个女保安就会分头到女厕所去找)。我的工作也并不是多么重要,无非就是溜到原材料仓库装摸做样核查或者是让工作人员检查一下是否相符,存量是否合理,能否及时跟上企划进度;或者是混到成品仓去看本应发到洛山矶的200个紫色插座是否被哪个大头的人搞成了蓝色的发出,而紫色的正随着货柜往纽约漂;唯一让我觉得我还有点价值的就是我必须翻译英文技术资料,对于我这个学会计的人来说,英文资料可不是随便就能溜或混成中文的,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看着开始不认识后来翻词典翻(我理解了为什么叫翻译)出来全是硅酸盐、石炭酸之类的物理化学名词,我只想自杀,好在人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看多了自然也就适应了。想自杀的日子里唯一的希望就是每到月末的最后一星期要核算应付帐款,这多少让我感觉到我还是一个会计,大学四年并没有白学,而当我理直气壮地纠正供应商错误的帐单时,我更认为我还是一名比别人稍微强一点的会计,这样想来,就会暂时忘却不能请假去报考注册会计师的烦恼,日子平添许多色彩。
休息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我怀旧似的穿上自己的衣服(不要以为我每天都穿别人的衣服,只要是上班,我们就必须穿厂服,男女老少全工厂一个样),大白天出去给我深圳的同学打电话(自从毕业就再未谋面,真的是咫尺天涯),刚说得高兴,看到保安在电话亭外向我招手,我匆匆丢下一句”保安在找我”,便飞奔回厂部四楼(那里是我的固定办公地点,常驻人员是老板加保姆外加三个董事长助理,还有一个传递文件的厂部秘书,其余人员如不是老板让保安传,不慎入内就得写检查),老板已经在那里发脾气了,检讨、挨训当然是少不了的,好在这些对于我都似家常便饭,我并没有觉得那是多大的一件事,我的同学可就吓坏了,她对所有那些她认识我也认识或者我不认识的人说:怎么办?春艳被软禁了!
她利用五一假期来东莞看我了,大学时的朋友S***R***H也在同一时间从兰州飞来了,她们说:这是一个监狱,你必须离开这里。S***R***H说:Now I know why the goods in ***merican is cheap, I feel sorry for my country and I would never buy anything from warmart.
我也最后决定离开了,代价是我必须放弃一个月的工资(这样才可以安全逃离),很多随身物品不能带走,我把所有我经手的事情写了一份详细的情况说明书,放在显眼的地方;那些优秀学生干部之类的证书就留下了,我把不得不带的毕业证、衣物简单收拾了一下,装在一个小方便袋中,从六楼(我住在五楼,与天空相接的地方被老板用铁丝围了起来)的阳台丢到相邻的大马路上,只听见“啪”的一声响,我的衣物、书籍散落一地,同学紧跟着贼似的东抢西捡,然后我从公司大门撒了个谎,穿着厂服出来了。我们三人立即上了开往深圳的大巴,我忐忑不安的坐在座位上,生怕哪个保安突然出现在车下,当大巴最终启动的时候,我感觉那是一九四九年。
客车从梅林关驶入深圳,看着宽阔的大路旁一座座葱葱郁郁的小山,我的心儿飞了起来。我热爱绿色,我更热爱绿色的城市。
进深圳的第一天我们直接去了欢乐谷,这时我才知道,人生还有另外一种活法。我同学上穿很贴身的T恤,下着一条七分裤,随意扎在脑后的头发在空中自在的跳跃,我羡慕地看着她阳光下熠熠生辉的脸,心底的意念更加坚定:我也要做深圳会计。在大梅沙,我对着永不停息的海水出神,同学问我在想什么,我回答:我在想,海的另一边是什么?“香港呗!”一句话将我拉到现实里,海的另一边只是香港,不是我想象中的世外桃源。
我必须马上找一份工作,这是快乐完了之后最迫切的事情。带着我最简单的证件,我开始在人才市场奋战。人才市场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如我一样忙忙碌碌,比我高大,比我时尚,比我有经验,手里拿的证件比我多可能也比我高级,还比我有力气,我就象一片树叶,被熙来攘往的人潮挤向一个又一个我想去或不想去的招人摊位。小心翼翼的询问,垂头丧气的离开,强颜欢笑,强打精神,强人所难……我这才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我是要做会计的,可我压根儿没有正儿八经做会计的经验,在深圳做会计需要深圳会计证,深户担保,还要什么办税员证,更不用提什么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暂住证,我上哪里找这些东西去。同学说,正的不行咱就来点邪的,办张假的深圳会计证去?可咱社会主义阳光雨露滋润下成长起来的名正言顺的会计为何要用如此卑劣的行径?难道深圳只欢迎邪门的聪明人?但另一方面,我一天比一天更热爱深圳,这里的基础设施多好啊:进上海宾馆旁的中心公园不需要门票,在天虹买东西可以用银行卡代替现金,随处都是atm机,坐公交车有专门的公交卡……我开始试着改变就业方向,仗着台湾厂对我非人的锻炼,我大胆的去光顾英文秘书、船务跟单、董事长助理等,这样一来,我的行情又有了一些回涨,可是我依然痛苦着,如果我放弃会计,如果后面的工作只是前面工作的简单重复,我离开东莞还有何意义?虽然苦一点累一点,但苦和累都是比较出来的,都是人自己的一种感觉;如果我放弃会计,就意味着我人生中最宝贵的四年白费了,这是我多么不愿意面对的问题。穿行在高楼林立的深南路,躺在我朋友蜗居的民房里,我痛苦并憧憬着:我要在深圳做会计。
我跑遍了深圳大大小小的角落,凡是通知我去面试会计,我一定去,福永、公明无一遗漏,我甚至想回东莞了。记不清面试了多少家单位,总之跑烂了我一双凉鞋,皮肤越晒越黑,心情越晒越糟,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沙头角保税区的一家日资企业通知我去上班,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一家,因为我记得面试时我明明白白告诉他们在此之前我一张凭证也没有做过。感谢天,感谢地,感谢阳光,感谢深圳,感谢所有我能想到的万物。
如愿以偿,我正式成为一名深圳会计。虽然工资比在东莞时低了,但是这里工作有大小星期,每天7.25小时,上下午各有十分钟休息时间,加班另有加班工资,下了班必须走,留在办公室会浪费资源。我仿佛一下子从地狱进入天堂:没有了被软禁的嫌疑,没有了老板阴晴不定的笑脸,没有了对随时可能会出现的保安的恐慌。
那是一段值得怀恋的日子,我的工作内容很简单却也是最地道最基础的会计工作:凭证制作。每天拿着一叠或多或少的原始凭证,到金蝶财务软件上做分录,然后打印、交课长审核,正确后装订。如果说在东莞练的是容忍力,在沙头角练的就是自信心,本来除了最基本的操作,我对电脑是一窍不通,财务软件只是在毕业实习的时候见过演示版,但是我赶鸭子上架,硬撑着头皮上了,没想到电脑还真通人性,刚开始见我的时候爱理不理,常常捉弄得我直想哭,后来看我天天与它打交道,竟然很给面子,不死机也不卡纸,对我服服帖帖;由着我拿着鼠标乱点,关键时刻常常会给我意外的惊喜。到月末的时候会忙一些,最多的时候我一下午做了80张凭证。让我感觉有点难度的就是最初的几个月每到月末要编制成本报表,几千种大大小小的冲压部品要从各自对应的原材料开始分析,半成品、在产品的期初数、期末数到后面的应销售数、实际销售数,单一产品毛利率,单一客户毛利率,弄得我头昏眼花,其实并不难,主要是麻烦,需要我细心、耐心,但是所有的报表都必须在次月5日前上交,否则我们的课长就拿不到按时上交报表的1000元奖金,我很有压力,就冲着课长成就了我深圳会计的梦想,也不能让他因为招了我而拿不到这1000元。加班算什么,没加班费的时候不也照样“两眼一睁,干到熄灯”?办公室密不透风,因为人少,空调是不会开的,六月的夜晚很热,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就象数不清的小虫在我脸上爬来爬去,我顾不上停下来洗把脸,只想着天亮前把表放到日本经理的办公桌上。
尽我最大的努力好歹在接近凌晨五点时完成了,匆匆忙忙走出工厂大门,保安慌忙拦住我打卡的手:等一下,再过5分钟就可以又算一个小时了(加班费按小时计,不足1小时忽略不计,例如1小时50分钟计1小时)!我报之以无力的苦笑,懒得说话,顺顺当当的打了卡,早上还要上班呢!凌晨的空气透着丝丝凉意,马路旁的长椅上躺着随遇而安的流浪者,做早餐生意的店铺师傅将面团在案板上甩得“啪啪”响,等待日出的夜色还要眷顾夜归的人。步行回宿舍冲完凉,同宿舍的工友已经起床了,望着她张成O字型的嘴,“我现在要去睡觉,请你在7:30分叫我与你一起去上班”……
沙头角是一个值得怀恋的小镇。它象内地一个宁静的小城,少了东门的喧闹与嘈杂,多了一份从容与静谧;它又象一位古典的江南美少女温柔而内敛,包容了深圳关内关外的优点却又不张扬外现。公司宿舍设在鹏湾二村,熟悉沙头角的人都知道,并不拥挤的沙头角将它所有的美景毫不吝啬的向世人展现。梧桐山是沙头角的底蕴,源源不断的绿色从那里喷薄;站在七楼的阳台上,明思克航母上旗帜飘扬,似乎正待起航,海天交接处的云海二十四小时变换着图案,永不雷同,迎面吹来的阵阵海风带着一点点腥味,那一刻我想去远方;楼下是个篮球场,在这里我生平第一次投进了篮球,虽然紧接着落地我就崴了脚;步行约五六分钟就是一个社区小公园,里面有山有水,错落有致,清晨,我通常会加入到老太太们的行列,跟着一起扭秧歌或者也跳跳中老年健身操(我同学总是以此为借口,对我狂扁一气);旁边就是新华书店,我装高雅的最好道具就是下班后会去书店走一走,可能有时候也只是因为吃的太多要帮助消化。
在沙头角做会计是我在深圳过得最充实的时光。浑身似乎总也有使不完的劲,睡觉前漫不经心翻翻的《武则天》一打开就合不上,到最后看完已是清晨,正常上班时我依然笑声朗朗;前一天晚上通宵加班第二天下班后照样跑去参加特区报社的英语沙龙;有时也会去上网,收发邮件结束后用“傻瓜”在鹏城聊天室与人胡扯;静下来的时候放放钢琴曲、听听校园民谣,游走在钢琴曲与淘米水中间,思绪在校园与工厂间反复,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幸福。
难得糊涂,人生很多事情都用不着深究。有工作,有收入,有闲暇,有快乐,课长也有奖金,我们也会定期得到邀请,去喝酒兼卡拉OK或去小梅沙游泳兼烧烤(虽然我都是凑热闹),还需要什么呢?我可以在沙头角呆上一辈子。美丽的日子总是走得太快,它不肯也不会为谁停留,公司上层领导决定将迁到关外去。在筹备的过程中,就有两个同事一周内分别丢了手机;新工厂旁边是杀猪厂,周围及深圳市区的猪肉都由那里供应,工作之外还可以去学一门手艺——杀猪;离最近的公交车站也有30分钟路程,这一切听起来都是那么恐怖。我热爱绿色的深圳,而不是被猪叫声环绕的关外;我热爱自由的深圳,而不是下班后哪儿也不敢去只能聆听猪的合唱;而且那时我正准备参加深圳会计证的考试,自信心不足报了培训班,寻求心理安慰坚持去上课,我要做持有上岗证的深圳会计。我对课长及日本经理说:让我走吧,我学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专业,干的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作,再招一个会英语的会计很容易,说不定还能说日语,那你们岂不是赚了? 我又一次选择了流浪,也就是从那时侯起,我开始痛恨我是个会计。进入人才市场,看到一大堆女的被挤得东倒西歪还在侍机行事往前靠,不用看那就是招会计的,我依然不是深户,没有深户担保,依然没有会计证、办税员证,脸上依然残留着稚气,以至于用人单位总以为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而将我的工作经验一笔勾销,几个用人单位尝试着让我去做他们的业务员,难道我这一生就死守着会计?我又开始动摇了。当一家培训机构通知我去面试英语培训助理时,我开始反省,我为什么要离开东莞,不就是为了做会计吗?我现在又去做助理是什么意思?不行,我还是要做深圳会计。当现任的老板问我有没有深圳会计证,我一下子情绪激动,“你为什么要问我有没有会计证?一个初中生、高中生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教育,随便报个辅导班就可以考过的证你为什么会问我有没有?我没有不是因为我没有能力,只是没有赶得上考试,难道就因为这个证你就可以把一个人从头到尾一笔勾销?” 于是我坐到了现在这张桌子前,继续着我深圳会计的生涯。自从离开了沙头角,就再也没有去上过培训班的课(为此又被我同学一阵狂扁:你多此一举),并于去年获得了深圳市电算化会计证、深圳会计证(虽然我对这两个证很不屑一顾,但是我不得不拥有它,还要把它当成职场的武器,我真的认为这是一种悲哀,是我的悲哀,也是深圳的悲哀)。
现任老板和财务经理都是早年国企外派的海归派成员,带着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作风接受了新式思想,提倡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公司给员工专门安排了集体宿舍,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最诱人的待遇是有专职的保姆负责一日三餐、宿舍卫生。公司同事的年龄从21-36不等,个个意气风发,身藏绝技。电视机的声音总是开到最大,从大唐情史一路演到尘埃落定;这边房间的音箱在放DISCO,鼓点声震耳欲聋;那边房间的CD里孟庭苇在问“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就似一名深闺怨妇;年轻点的惦记着周末是去本色还是无心快语吧,30左右的则想着买衣服是去华强北还是东门,还有几个边说边唱浩浩荡荡开到办公室卡拉OK,有家属的男士谈起中东局势一套一套,没家属的男士与女士谈酒经,互相讽刺、互相吹捧,时不时加上一两句贸易术语,形象的比喻引发出阵阵大笑。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可是我更加怀恋沙头角。繁华的罗湖给了我生活的便利,却不能给我一块宁静的天地;一杯杯酒精下肚,看着迪厅里男男女女群魔乱舞样的疯狂扭动,我更加怀恋昔日的老太太们的中老年健身操;东门商场里天天劲吹打折风,令人眼花缭乱的衣服催动着人们无穷的欲望,挣多少钱才是尽头?怎样才能一夜暴富?不暴富怎样才能傍大款?而我只是一名会计,一名深圳小会计,有着不管私底下跟你怎样风雨同舟总得恭恭敬敬尊称为经理的同事,看着橱窗里的衣服想象自己穿上会是什么模样然后恋恋不舍的走掉。整天与金钱打交道,但对于我来讲,它只是一种概念,一种于我无任何意义的库存商品。灿烂的灯火从不停止炫耀这座城市的辉煌,我变得越来越浮躁、越来越迷茫,我害怕哪一天我也会沉到酒缸里,消失在烟雾里,我当前最需要的只是一张书桌,可以让我安静的写日记、想心事、发呆。
日子在做凭证、写支票间流失,不咸不淡的生活总渴望着奇迹,梦里走了很多路,醒来还是在床上。终于鼓起巨大的勇气,找了一本《税法》,半躺在床上,假装是看小说一样的看,“你在看啥?”来自东北的同事从外面逛街回来了,例行公事关心一下我,看到我在看书,以为是什么好东东,“好啊,你,自己躲着看,给我看看,是不是《非常日记》那样的?最好是比那还刺激,噢!我晕倒,你竟然在研究睡觉的方法?太不可思议了!”
又到了一年岁末,老家亲戚打电话来旁敲侧击的询问对象之事,我正式沉默了。深圳日益增多的大龄青年从不放弃傍大款、陪富婆的梦想,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难以沟通,在这个盛产快餐的城市里我们不愿意也不敢去相信偶尔相逢的陌生人,当他问你“佛洛伊德是不是卖电话机的”,当他问你“葫芦僧是什么东西?”胡说八道的交流日盛凸显正式交流语言的贫乏。站在现实的土地上,总渴望着有一两只小鸟从头顶上飞过,让我的思绪做一回短暂的旅游。我的活力正在一点点消退,青春易逝,三年的社会生活将一个自命不凡的学生正式变成了一粒尘埃,与本已存在的千万粒尘埃一起自生自灭。看着乱糟糟的集体宿舍,我想:等我将来有了自己的小窝,我一定把它收拾的干干净净,整洁温馨,可是我自己的小窝在哪里,哥哥嫂嫂的家只是我探亲的驿站,飘来飘去的树叶最终遁入泥土,可是我将消失何处,如果突然沾染上一种流行病,贫穷的我将如何应付;唯一的安慰便是不在倚靠同学的救助,穿上了花花绿绿的衣服。
“讨论一个问题,确实无法支付的应付帐款计入资本公积,要不要交所得税?”我在给我同学打电话,“不知道,喂,我新从网上下载了一个菜,叫恭喜发财,你星期六过来尝一尝,给个面子嘛,别学傻了!”深圳唯一的同学基本上这样对付我,“别考什么注册会计师,找个老公安居乐业!”见了面,她总是这样教训我。
或许她是对的,但是在深圳这个地方,我的人就跟我的职业水平一样,找一份差一点儿的工作可以,但是找不到好老公,既然不能爱别人,那就先爱自己吧。没有一张安静的书桌,就在喧闹中寻找安宁的心境,没有人答疑解惑,就假装厚着脸皮陪这假笑上中华会计网,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好心的人或严厉、或慈眉善目、或不屑的回答,无论他门脸上藏着什么样的表情,对我都是提供了一种帮助,我感谢他们,我更敬重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一个深圳小会计,考中级经验不够,做主管城府不够,喜欢与数字打交道,喜欢被人领导,爬行在通往注册会计师的小道上,渴望着小会计变成大会计。
............试读结束............
查阅全文加微信:3231169 如来写作网:gw.rulaixiezuo.com(可搜索其他更多资料) 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3231169@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3231169@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gongwencankao.com/4544.html